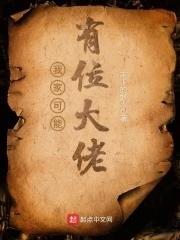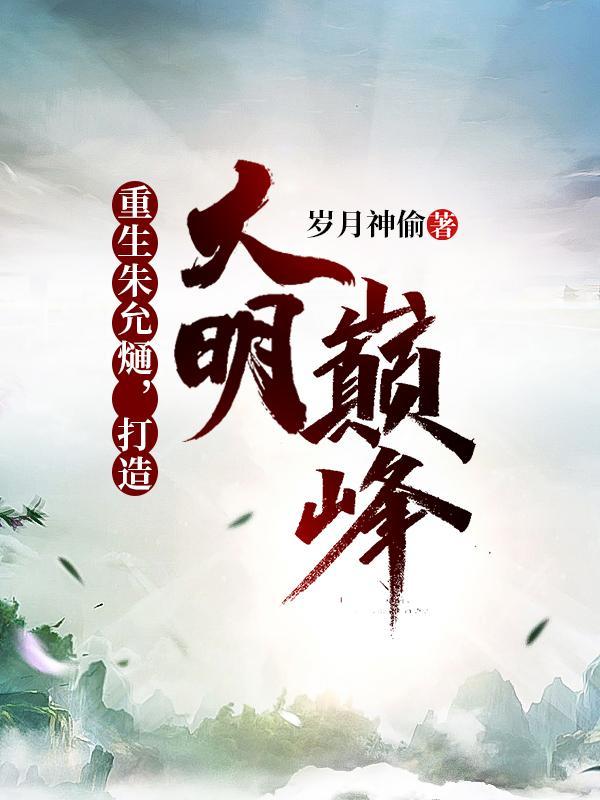看玄幻小说网>捉妖 > 第766章 离地焰光旗(第2页)
第766章 离地焰光旗(第2页)
有人说西北戈壁出现一座“无名学堂”,学生不分贵贱,课程只有一项:静听内心之声。
有人说南海礁石每逢月圆之夜,会自发奏响一支残缺却温暖的笛曲。
更有传言称,昆仑雪顶的石碑每当下雪,字迹便会渗出血痕般的红光,映照出一段无人识得的乐谱。
而最令人震惊的是??归墟谷中的小玉钟,在某个无星之夜,突然升空,化作一道流光,射向四面八方。待人们追寻其踪,才发现那光芒竟分裂成千万点,落入每一座村庄、每一条街巷、每一个屋檐之下。凡是被光点触及的器物??锅碗、门环、井绳、纺车??皆能在特定时刻发出独特声响,仿佛被赋予了灵性。
百姓惊疑,官府震怒,立刻下令收缴“妖器”。可越是禁止,这些日常之物发出的声音就越发清晰,甚至能在深夜自动共鸣,形成连绵不断的和声。有人试图熔毁一口发出童谣的铁锅,结果火焰中竟传出百人齐唱《摇篮曲》的旋律;有县令砸碎一面响铃的窗纸,当晚全家梦见自己跪在万人之前忏悔贪污罪行。
恐慌蔓延之际,一道青驴身影再度出现在世人视野。
萧景知骑驴行于市井之间,不再吹笛,也不言语,只是静静走过。他所经之处,禁乐器具纷纷自鸣,却不扰民,反似安抚。孩童见之欢呼,老人见之落泪,囚犯闻声痛哭伏地,狱卒亦为之动容。
朝廷派出三十六名乐官联合施法,欲以“正音咒”镇压乱象。他们在皇城中心筑起九层音坛,引北斗星光注入青铜巨磬,誓要重建“天籁秩序”。然而当磬声响起时,整座城池的锅碗瓢盆同时应和,奏出一首荒诞却真挚的市井交响曲。百姓非但不惧,反而纷纷走出家门,敲打着手中物件加入其中。一夜之间,京城成了最大的鸣社。
皇帝震怒,召集群臣议策。有老臣泣谏:“昔年薛无音以恨铸钟,终致崩塌;今若再强求统一之音,恐重蹈覆辙!”
年轻宰相冷笑:“乱世需重典,岂能任由百姓信口开河?”
唯有太医院首座沉默良久,终起身道:“陛下,十年前药医带回的记忆香曾显示??真正治愈病患的,并非灵丹妙药,而是他们终于敢说出‘我害怕’三个字。或许……声音本身,就是一味药。”
帝默然。
三日后,圣旨下达:废除一切音律管制,赦免所有“乱音”罪名,开放民间自由创制音律。并诏告天下:“自今日始,九州之内,人人皆可为乐师,处处皆可成鸣社。”
旨意传出当日,玉钟残影再现归墟谷,这一次,它并未停留,而是化作一道虹桥,横跨天际,连接昆仑、南海、西域、东海四极。桥身由无数闪烁的“声”字构成,每一字皆代表一段真实说过的话语。
桥成之时,第八人立于桥头,手持赤玉埙,面向苍穹。
他没有吹奏,只是将埙高举过顶。
霎时间,天地共振。
昆仑积雪崩落,露出深埋地底的古老琴柱;
南海龙宫开启,献出千年封存的潮汐鼓;
西域沙漠升起十二座沙钟塔,随风自鸣;
东海群岛浮现出沉没已久的“言舟”,船上刻满失传的祷文。
八方呼应,万籁齐鸣。
而在这一切之上,那枚曾藏于石碑中的心埙,终于发出第一声完整的“亡声”。
它不像雷鸣般震撼,也不似凤唳般清越,而是一种极柔和、极深沉的震动,仿佛整个宇宙在轻轻叹息。这声音穿透时空,抵达每一个曾因恐惧而沉默的灵魂耳中。
于是,有人开始说话了。
一个哑了二十年的村妇,在田埂上突然开口,说的是她女儿幼时最爱听的故事;
一个被判死罪的刺客,在刑场上大笑三声,喊出自己真正的名字;
一位隐居多年的前乐官,焚毁所有乐谱,抱着孙子教他用筷子敲碗唱歌;
甚至皇宫深处,那位从未开口的皇后,也在夜雨中轻声哼起儿时乡谣。
世界并未因此变得完美。争吵仍在,误解尚存,恶意也未消失。
但至少,人们不再害怕表达。
多年以后,史官修撰《音纪》,记载这段岁月时写道:“自礼魂钟碎,至共情桥立,凡十三载。其间无大战,无大疫,唯人心渐苏,言语复苏。百姓不复以音律为枷锁,反视其为血脉延续之桥。是谓‘声兴则民醒,言畅则国活’。”
而在那座无匾的西北学堂里,第八人依旧每日点燃一炉香,让学生围坐静听。
一日,有个少年忽然问道:“老师,如果我们说的话,终究改变不了世界呢?”
青年望着窗外黄沙漫天,良久才答:“改变世界的,从来不是一句话的力量,而是千万人敢于说同一句话的勇气。”
话音落下,风穿过廊下悬挂的铜片,叮当作响。
那一瞬,仿佛有谁在远处吹响了短笛。
青驴蹄声渐远,融入天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