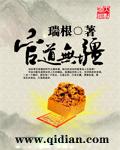看玄幻小说网>大宋文豪 > 第391章 恩威并施张弛有度(第1页)
第391章 恩威并施张弛有度(第1页)
夜色已深,白日里的喧嚣散去,外面的街道上只余下几盏灯笼在夏日的晚风中轻轻摇曳。
澄明斋前铺内,烛火微明,陆北顾与沈括对坐于案前,中间摆着一壶刚点好的茶。
“这么说,这事已经定了?我也得跟着。。。
李星星的信被轻轻夹进“后来者回信集”时,若兰的手指微微颤抖。那几行歪斜却用力的字迹像一根细针,刺进了她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她将册子合上,放进檀木匣,又缓缓抚过匣盖上的“昭义同人”印章??这一次,她仿佛听见了百年前梅岭雪夜中那一声轻咳,和药炉旁低语的回应。
春日的阳光洒在实验学校操场边的樱花树上,粉白花瓣随风飘落,落在孩子们尚未写完的信纸上,沾在他们的发梢与肩头。若兰站在一旁,看着老师们把一封封稚嫩的信收进特制的陶罐里,准备埋入校园东角的“时间花园”。每一年春天,这里都会种下新的希望:去年埋下的种子已长成小树,而那些信,则将在三十年后由下一辈的学生亲手开启。
她正出神,林舒走了过来,手里拿着一份文件。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刚发来的通知,”她说,“‘心光’课程第二阶段正式通过评审,未来五年将在全球一千所试点学校落地。他们特别提到,要以‘李星星之信’作为情感教育模块的核心案例。”
若兰点头,却没有太多欣喜。她望着那个蹲在花坛边、正用手指抠着泥土的小男孩,低声问:“他今天没去心理辅导课?”
“去了,但只坐了十分钟就跑出来了。”林舒叹了口气,“社工说他抗拒亲密接触,害怕再次被抛弃。他已经转到我们学校的特护班,可问题不在知识学习……是在信任。”
若兰慢慢走过去,在李星星身边坐下。男孩没有抬头,只是机械地把土堆成一座小山,又用手掌抹平。
“你知道吗?”她轻声说,“我小时候也觉得自己没人要。”
男孩终于抬眼,带着怀疑。
“我母亲早逝,父亲常年在外工作。有几年,我住在亲戚家,每天早上醒来都怕自己做错了什么,会被赶出去。”她笑了笑,“所以我总拼命讨好别人,哪怕别人对我很凶,我也笑着说没关系。”
李星星怔住了。
“后来我才明白,不是我不值得被爱,而是那时候的世界还没准备好接住我。”她从包里取出一张照片,递给他,“这是王小川十岁时拍的。你看他笑得多勉强?他妈妈在他六岁那年改嫁远走,爸爸酗酒打人。但他还是写了那封信,因为他相信??总有人愿意听。”
男孩接过照片,指尖轻轻摩挲着边缘。“他也……一个人?”
“是啊。可你看现在,他的信成了千万人的灯。”
一阵风吹来,卷起几片樱花,掠过两人之间。李星星忽然小声说:“我想再写一封信。”
“好啊。”
他站起来,跑回教室。不一会儿,捧着一张新纸回来,坐在原地一笔一划地写。若兰没有看,只是静静陪着他。等他写完,递过来时,她才低头读:
>“亲爱的王小川哥哥:
>我叫李星星。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,但谢谢你写了那封信。我现在还不敢相信有人会一直陪着我,但我愿意试试看。如果你能收到这封信,请告诉我:你是怎么不怕孤单的?
>??李星星”
若兰的眼眶热了。她把信小心折好,放进随身带的小布袋里。“我会替你寄出去的。”她说,“虽然他可能不会回信,因为已经过去很久了。但你知道吗?有时候,写信本身就是在回答问题。”
那天傍晚,若兰回到嵩山文化园办公室,打开AI虚拟陆北顾系统的后台日志,发现一段异常记录:凌晨三点十七分,有人匿名输入了一条极长的问题,系统用了整整十二分钟生成回复。她点开查看:
**用户提问:**
“如果一个人从小就被否定,从未感受过善意,他还能学会爱人吗?还是说,伤痕太深的人注定只能伤害别人?”
**系统回复:**
“百年前,我在皖南山村见过一个孩子。他偷米被抓,脸上挨了一记耳光,却始终不哭。我问他为何不逃,他说:‘跑了也没地方去。’我把半袋米送他,他盯着看了很久,最后说:‘你会后悔的。’??他以为所有给予都是骗局。
可三年后,他在暴雨夜里背一个发烧的女孩走了十里山路求医。人们问他为什么冒险,他说:‘因为她哭的时候,让我想起那时候的自己。’
伤痕不会消失,但它可以变成理解他人的桥梁。你不必立刻相信世界是暖的,只要允许自己保留一丝疑问:也许,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