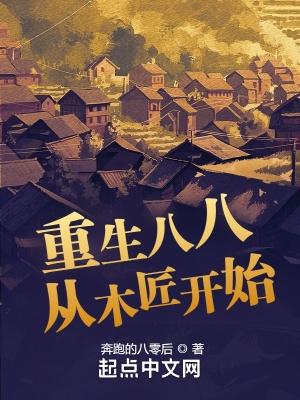看玄幻小说网>太子她只想登基 > 6070(第23页)
6070(第23页)
“说来,曹阁老是斐儿的亲舅祖,可碍着礼数,见了面也只是拘谨客套。公主出入宫闱比我方便,若得空了,便带他去多探望探望罢。”
永嘉公主闻言点头:“我晓得。是该多亲近亲近,我们身上都淌着曹氏的血脉呢。”
谈及血脉,永嘉公主感慨伤怀:“若哥哥还在,看着斐儿健康长大,咱们一家人其乐融融,多好啊。”
她顿了顿,不禁又想起来晏朝:“大嫂不知道,前些日子父皇宣召了东宫那位选侍——就是从前斐儿跟前的疏萤,还叫我去劝她绵延子嗣之类的。若东宫有了后嗣,只怕地位要更加稳固了。”
孙氏却断然摇头:“子嗣?不会的。倒是可怜了疏萤,那样好的一个女孩子,可惜白白糟蹋了。”。
信王安分消停了几个月。王府新换了个宾辅,其人在朝中地位平平,论起才学却是德高望重,乃当世大儒。于是信王便借着闭门思过的名义潜心修读,闲时或醉心书画,或策马游猎,瞧着倒真像是个闲散王爷了。
近来,信王还给皇帝引荐了几名道士,听说皆是道家大师。其中一名吴天师年逾古稀,仍旧耳聪目明、身体健朗,传言他隐逸山林,潜心修道多年,道行和修为极高,还能炼就延年益寿的长寿仙丹。
皇帝试了道士进献的丹药,果然觉得神采奕奕,不免又动了修道的心思。
这倒不稀奇,近两年皇帝发觉身上衰老的迹象越来越明显,即便是尤为注重保养,也耐不过岁月跎蹉,是以四处寻求延寿之法,亦不时打坐修心,对道家极有好感。
只是这一回,皇帝显然更加痴迷。不仅常常驾幸西苑的清馥殿,且丢下了不少政务,开始悉心钻研起道学。
恰巧天气日渐炎热,皇帝故技重施,说身子不适,需提前搬离大内。而这一次,皇帝要去的地方,却不是南台。
兰怀恩提议,西苑仁寿宫还有几间宫殿还空置着,稍加修缮即刻居住,不必太过靡费。且宫殿离太液池近,清爽宜人,更重要的是远离繁务又靠近清馥殿,修心练道再合适不过了。
消息一出,遭到了朝臣的一致反对。
去岁皇帝执意去南台时,大臣们尚且不同意,更遑论更加偏远的西苑。况仁寿宫附近有先蚕坛、桑园等场所,清馥殿附近又是牲口房,是豹子、老虎等野兽驯养的地方,如此鄙陋的场所,堂堂九五之尊住进去,岂不荒唐?
皇帝知道那些臣子的脾气,索性一连几天朝会都不去了,也不再去文华殿,连奏章都是经司礼监“精心”挑选过的才批阅。
但圣旨毕竟还没有下,皇帝和朝臣仍在僵持。一众廷臣伏阙于乾清宫外,誓不罢休。
皇帝气急,挥手将一摞奏章掀翻在地,指着兰怀恩冷冷下令:“去!叫东厂的人将他们都赶走!要跪去午门外跪着,别在这里碍朕的眼。”
兰怀恩领旨出去,见为首的竟是太子,一时间颇觉为难。他知道她的脾性,同时也明白皇帝的决心。这会子太子若执意觐见,皇帝发起怒来还不知是何后果。
他自然希望她的委屈少一些,便上前低声劝道:“圣意已决,太子殿下再劝也是徒劳,又何苦呢?”
晏朝果然无动于衷。
兰怀恩暗叹一声,退几步,高声道:“陛下圣谕,诸位大臣要跪,请到午门外继续跪着。”
旋即朝左右一点头,太监们立时涌上前去,一时间推搡声、吵嚷声、嚎叫声杂乱无章,乾清宫外乱作一团。
宫殿内,瓷器碎裂的“咣啷”响起,紧随其后是皇帝的怒吼:“叫他们滚出去吵——”
然而太监们并不敢动太子。不一会儿,便有个内侍出来通传:皇帝宣太子进去。
兰怀恩心道不好,却也不敢阻拦,只得忧心忡忡地看他进去。
进殿时,内侍正在收拾满地狼藉。一些奏本被水溅湿,散落开来,上头的字迹都已有些模糊。晏朝亲自接过内侍怀里抱着的一摞奏本,毕恭毕敬奉上去,才下拜行礼。
皇帝阴沉着脸,额上青筋隐现,显然怒意未消:“太子也敢拦着朕么?看来朕之前那三十记板子打得轻了,这么长时间,一点记性都没长。”
晏朝垂首道:“父皇息怒。仁寿宫远离大内,理政多为不便,且环境僻陋,实非天子可居。儿臣与朝臣们是为您声誉着想,父皇励精图治,天纵英明,倘因此事惹天下非议,岂非有损一世圣名?还望父皇三思而行。”
皇帝嗬嗬冷笑:“为朕着想?夏日酷暑难耐,朕日夜理政,头眩体虚,就连换个凉快的地方都不能么?朝中那些大臣在郊外还有避暑别宅呢!连你也知道出宫去舒坦,现在却来指责朕!一个个成天把为朕分忧挂在嘴边,这时候了连朕挪个地方都咬死不松口,一帮子老顽固跪在外头要挟朕,让朕如何心安!”
一本奏章猝不及防砸过来,晏朝忙捡起来合上,还未回话,才缓过气的皇帝指着她,劈头盖脸一通怒斥。
“还有你,没心没肺的东西!为人臣为人子,半点也不体察朕心,忠孝之道都吃到肚子里去了?仗着储君的身份,伙同群臣伏阙逼谏,你以为朕看不出来你是何居心么!”
皇帝显然是将几日以来积攒的愤怒都发泄到太子一人身上了,一时间,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天子威仪风度,将满腹不满一股脑儿倾倒出来。
“……太子去年在南京私下里做的那些事,以为朕没追究,就是全然不知么?朕念着你初次南巡,新政启行,给你留足了面子。不想你如今得寸进尺,肆意专横,竟敢作起朕的主了!朕给你恩典,不是叫你今日跪在这里违逆朕的!”
晏朝后脊发凉,皇帝果真是怀疑的。她呼吸微窒,即便知晓此刻喊冤也是徒劳无功,但总归绝对不能认下,忍不住开口:“父皇明鉴,儿臣不曾——”
“朕不想听你狡辩!”皇帝脸色铁青,胸膛剧烈起伏,他猛一拍案:“人人都称颂太子贤明端正,朕瞧着倒未必。否则,如何连宁妃那样温婉贤淑的养母都疏远了你,足见你只是表面功夫做得好!”
此言一出,晏朝心头乍然一凛。她全身颤抖了下,一时竟无言以对。
皇帝不知何时已离了座,站在她面前,居高临下冷睨着她:“怎么,朕没说错罢。你同你母后一样,她是假仁慈,你是真虚伪。”
晏朝登时浑身气血上涌,霍然抬起头,仰面直视着皇帝,一字一顿咬出来:“母后正位中宫十三年,素有贤名,况父皇赐的谥号正乃‘温惠’二字,如今既认为名不副实,不妨昭告天下,改谥如何?”
皇帝如何听不出这弦外之音,暗讽他不顾声誉,又怨怼他贬低皇后。